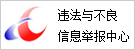元朝至顺二年(1331)春,回乡“闲居养疾”的前总管王穆收到其“乡弟”罗山教谕张叔英(见文末注释)的来信,信中满载霍邱“耆宿儒学”们的深情嘱托,希望他能为县里刚刚落成的城隍庙题写碑记,“勒石于庙,以图远传”。
读罢此信,王穆“惊且喜”,于是欣然命笔,作《城隍庙碑记》(以下简称“《碑记》”)。该文载于万历《霍丘县志》第九册,这也是目前可见有关霍邱城隍庙的最早文献资料。
根据《碑记》,这座大型建筑于是年正月初开工,二月末完竣,前后耗时不到两个月,且是在寒冷的冬季。这座久经风雨的庙宇已有近七百年历史,其部分建筑至今犹存。

霍邱城隍庙今貌
霍邱的城隍庙是谁建的?为什么建?
第一个问题,《碑记》说得清楚明白:城隍庙的倡建者是当时的承事郎达鲁花赤,名叫怯列。“达鲁花赤”是蒙古语,意为“掌印者”,是蒙古国历史上的一种职官称谓。元代规定汉人不能担任官吏系统中的正职,因此朝廷各部以及各路﹑府、州、县均设有达鲁花赤,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,掌控实权。
据万历《霍丘县志》第五册《秩官》载:“宋嘉定十六年(1223)蒙古初置达鲁花赤治县”“元(霍丘)设达鲁花赤一员”。霍邱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达鲁花赤共两位,一位是昔里吉思,另一位就是怯列。由《碑记》可知,怯列在霍邱为官三载,颇有政声。为了尽快建成城隍庙,他“首捐己禄”,官吏士绅纷纷效仿,在强大的感召力下,修庙既未影响市肆交易,也未影响农时耕播,仅一个多月便巍然完竣,“神人俱依”了。

接下来的问题是:当政者为何要花费气力,用“公权力”去修筑满足民间信仰的城隍庙?
首先,按照王穆总管的个人理解:一城之中,有人则必有神,神必定会保佑那些对其虔诚的信徒;神祇与知县(达鲁花赤)各有分工,前者负责“理幽”,后者负责“治明”,这一“幽”一“明”几乎囊括了百姓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。道理说起来简单,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,至少为民“理幽”的场所仍是空白,如今怯列率民筑庙,他对待神明尚且如此敬重虔诚,那么对待老百姓的“宽广仁爱”也就不言而喻了。这段话,虽是《碑记》所载的王穆的个人观点,却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官绅阶层的普遍认知。
其次,是以怯列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复兴传统,分步实施“建筑教化工程”的结果。王穆在《碑记》中详述了“近年来”霍邱城从“庙制屺坏”到“渐次创立”的过程:一方面,天历三年(1330)春,他回“安丰旧庐”闲居养疾,只要听到地方官有嘉言善政,他便欢欣鼓舞,“如炎而凉,如渴而浆,如口出而身履,如屠门之大嚼”;如若不然,便“心怀戚戚,数日不能排遣”。俗话说: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,这究竟关自己什么事呢?大概是“人心思定,天道公理去人心不远”吧;另一方面,想必来信中张叔英教谕也对“近年来”霍邱的建设情况做了详细介绍,于是他复载入碑,以彰其德:
一、文庙聿兴,则士风励,而人知所以劝学矣;
二、三皇殿成,则播植繁,而民知所以务本矣;
三、复修县厅,是堂高政平,民知承惠而讼简矣;
四、又修馆驿,是送往迎来,民知致廪而敬上矣;
五、再修尉司,为治之所,是盗所屏息,民知安其居矣;
六、虽忠显吕尚书祠堂,犹加缮完;
七、经营城隍忠佑辅德大王之庙,是祸福昭彰,雨旸时若,民知乐其业矣。
不难看出,这项“建筑教化工程”是计划井然、分步实施的,其目的依次为劝学、务本、讼简、敬上、安居、乐业,可谓统筹有法、指向明确,其中宗教建筑有两座:三皇殿和城隍庙,前者主祀天皇、地皇和人皇,也就是远古时期的三位杰出氏族领袖——伏羲氏、神农氏和轩辕氏,修筑目的在于劝农务本;相比之下,城隍庙略有不同,其主祀“忠佑辅德大王”,也就是俗称的“城隍爷”,他是古代民间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,也是道教的重要神祇之一。

《碑记》中王穆对这七座建筑的描述还有三点值得留意:一是城隍庙的修筑用的是“经营”二字,也即初建,不同于吕尚书祠堂的“缮完”;二是这七座建筑都是达鲁花赤怯列所主持,当然,也离不开令尹杨承事、主簿康将仕、典史高安富等共襄其事;三是筑修的出发点是“为民创制,非徒观美而已”,整体格调是实用大于审美,突出其现实功用。
这座城隍庙的造型如何?且听下回分解。
注释:万历《霍丘县志》第九册《记》作“张叔英”,乾隆《霍邱县志》卷九《艺文》作“张淑英”,同治《霍邱县志》卷十四《艺文志》亦作“张淑英”,今从明志,河南罗山人,曾任霍邱教谕,生平事迹不见于诸种《霍邱县志》之《秩官》。
 皖公网安备: 34152202000106号
皖公网安备: 34152202000106号